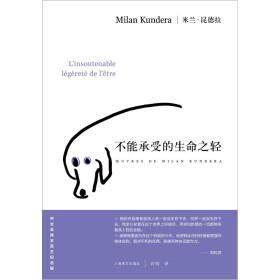
說起米蘭·昆德拉這部小說《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其實在中國早就有很多,據說光是我手上這個版本,這樣一個譯本,現在已經賣出過百萬冊了,累計起來,也不要談以前有一些盜版,或者再以前有像韓少功先生從英文翻譯的版本。既然如此,大家應該都非常熟悉這本小說,我為什麼還要重頭去介紹他呢?這一來是因為我最近注意在被邀請去介紹這個新的版本,然後我注意到這個版本譯的非常好。更重要的是我覺得在現在這個時候,重新去讀昆德拉這部小說是有特別的意義,會給我們特別啟發。
我們今天這個時候是什麼時候呢?各位,是個反三俗的時候。反三俗是哪三俗呢?我老是記不清,庸俗、低俗、媚俗,雖然我不大搞得清楚這三俗仔細的區別是什麼,反正我們就叫它反三俗。說到反三俗運動,我就不能不想起這部書裡面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曾經的中國的很多知識分子把它掛在口上,就是Kitsch,一般中文把它譯成媚俗。昆德拉在這部小說裡面,對這個媚俗這個觀念做了相當精彩的闡述,到底什麼叫做媚俗呢?媚俗是不是我們現在反三俗裡面反的那個媚俗是同一個意思呢?其實不是,為什麼呢?因為這裡面所講這個媚俗,是來自德國人那個Kitsch,它有一套獨特的含義,當然經過昆德拉自己的創造性詮釋。
我們在這裡面看一看,他舉個例子,他說到小孩的時候,常常看那些歐洲給小孩看的有插畫的舊約聖經。他就注意到這裡面的上帝,他是個很慈祥,鼻子上面拖著長長的白鬍子的老人。他就想既然上帝長了一張嘴,那麼他應該也吃東西,既然他吃東西,那麼他必然會有腸子。可我馬上被自己的想法嚇壞了,因為我說出了一個生於一個可以說不信神的家庭,但是琢磨上帝是否有腸子,豈不是褻瀆神明嗎?因為有腸子的上帝,豈不是表示上帝要拉屎嗎?糞便是一個比罪惡還要尖銳一個神學問題。上帝給了人類自由,因此可以斷言上帝不該對人類種種罪行負責,但是糞便的責任得由人類的創造者獨資來完全承擔。
說完糞便,我們再來想另外一個重要的神學課題就是性愛。這裡面他就說到,以前歐洲的神學家曾經爭辯過,到底亞當、夏娃會不會在伊甸園裡面做愛呢?有人就說不會。但是後來有一個九世紀有名的神學家就是斯科特,他就說不,亞當是可以任意的像我們伸出大腿跟手背一樣,隨意讓自己的陽具勃起。那麼千萬不要以為這個觀點是表示一個很褻瀆的想法,其實不是的。這位神學家了不起的地方在於他想說的是在亞當而言,他的陽具是像隨意肌一樣隨意控制隨意勃起的。因此他這個勃起是要勃起就勃起,而跟興奮無關,也就是說他會跟夏娃就算做愛的話,不是出於一個性的興奮,不能控制的興奮,而是出於什麼呢?出於大腦的命令,是一個理智指揮的過程。
也就是說,我們看總結一下,剛剛我們看到那樣一個神學世界是什麼世界?是個亞當跟夏娃會做愛,會生小孩,可是他們沒有性快感,沒有性興奮。上帝有嘴巴,有鬍子,但是他呢,甚至可能還吃東西,但是他不會拉屎,一個要把糞便跟性快感排出去的這麼一個世界是什麼世界?這是一種對生命的絕對認同,把糞便被否定,每個人都視糞便為不存在的成為美學的理想,這個美學理想就是Kitsch,就是我們講的媚俗了。所以他就說了,究其根本而言,媚俗是對糞便的絕對否定。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的就是昆德拉一個典型小說裡面夾敘加議的風格,這是他很喜歡的,寫一段故事,寫著寫著就開始忍不住要大發議論,這個議論者到底是他本人,還是這個小說的敘事者呢?常常我們會被他搞混了。我們現在又回到這個故事了,這個故事裡面很有名的女主角薩賓娜是一個畫家,對不對,這邊說到薩賓娜內心對共產主義,當然講是過去當年捷克那個共產主義,最初反叛不是倫理性的,而是美學性的,令她反感的遠不是世界的醜陋,而是這個世界所帶的漂亮面具,換句話說就是媚俗。五一節就是這種媚俗的典型。然後他就說五一節的遊行,捷克當年搞那種五一遊行,很盛大,很漂亮,形形色色的衣服,彩旗,大家非常快樂的、慢慢的接受檢閱。然後這裡面說到遊行隊伍走進主席台的那一刻,即使是最愁苦的人都馬上露出燦爛的笑容,好像要證明那是他應該有的喜悅,或者更確切的說是要表達他們應有的贊同,這並非是一種簡單的對共產主義政治的認同,而是對生命應有的認同。五一節吸取的是對生命的絕對忍痛這個生生泉源,所以遊行隊伍中人們發出心照不宣的口號,並不是共產黨萬歲,而是生命萬歲,它之所以有力量,就在於它奪取這個口號了。恰恰是這個愚蠢的同意反覆,驅動著遊行隊伍中對共產主義思想仍舊完全無動於衷的人們。
可是我們要瞭解昆德拉這個作家,他是一個對政治非常敏感的作者。他有時候,甚至你會覺得他非常犬儒,你說他當年是不是一個很反共的流亡分子作家呢?其實他並不是,反過來他也不會因為到了法國居住,然後就一面倒的歌頌所謂西方自由世界的理想。你看這裡面就說到薩賓娜後來移居到美國的時候,有一個朋友是美國的參議員。這個參議員開著車,後頭帶著四個小孩,然後放著小孩出來,在草坪上玩,太陽底下,非常快樂天真爛漫的快樂的玩著,然後他就用做夢似的神態,看著正在奔跑的四個小小的身影,轉頭對薩賓娜說,看看他們,我說這就是幸福。這幾個字呢,就是指的薩賓娜在這一刻彷彿看到參議員站在布拉格廣場一個主席台上,臉上掛著微笑,與共產黨國家領導人站在高高的主席台上對腳下遊行隊伍中同樣微笑著的民眾發出的微笑一模一樣,因為這也是一種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