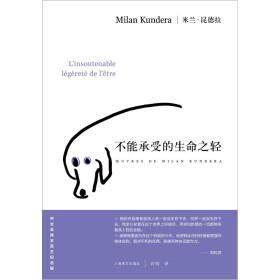
閱讀一個地方的報刊,我很喜歡留意常用的形容詞與副詞,尤其是那些和情緒相關的字眼。它們就像電郵和手機短信裡的表情符號,是一套數量限定的格式,用來表達這個地方最常見或者最受歡迎的情緒傾向。憑我多年翻閱大陸報刊的經驗,我發現「激動」和「動情」是出現頻率相當高的詞,一般用來形容某些被訪者說話時的語氣,或者被用來形容受訪者的心情。比如說:「看到解放軍戰士進災區的雄姿,我非常激動」;「聽見領導這番話,我很激動」。又或者,「老人動情地表示,社會對他的關心,他永遠難忘」;「大橋落成那天,他動情地說,這輩子的心血總算沒有白費」。
我還發現,凡是「激動」和「動情」派得上用場的地方,必定是些很「正面」很「激動人心」的場合。它也許是天災過後一位領導不辭勞苦地跑來現場親切地慰問災民,也許是一位勞動模範堅守崗位矢志不渝地服務人民。總之它不會是負面的,不會是一個考試考壞了的學生很「動情」地表示,自己的一生完蛋了;更不會是一個盜匪被捕時說,「被警員踩在地上的那一刻,我覺得非常激動」;儘管他們在那一剎那還真的十分激動。
假如你聽說今天的中國人變得很無情很冷漠很犬儒,不願相信任何崇高的理念與價值,那麼你就真該多看點報紙多讀點新聞了。這些文字裡的中國人,是一群天真純良的好人,並且十分浪漫,總是會為一些正面的消息而激動,總是會為一些好人好事而動情。
最近流行「反三俗」,可是我連那「三俗」裡的「庸俗」「媚俗」「低俗」都分得不大清楚。所以我拿起了米蘭·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因為正是這部經典小說,把源自德文Kitsch的「媚俗」變成了文化界的關鍵詞。在解釋什麼叫做「媚俗」的時候,昆德拉舉出了當年捷克共產黨政府慶祝「五一」勞動節的例子:
「那個時代,人們表現都還積極或儘可能有積極的表現。……遊行隊伍走近主席台的那一刻,即使是最愁苦的人都馬上露出燦爛的笑容,好像要證明那是他們應有的喜悅,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要表達他們應有的贊同。……五一節汲取的是對生命的絕對認同這一深深的源泉,遊行隊伍中人們發出的心照不宣的口號,並不是『共產黨萬歲』,而是『生命萬歲』。……恰恰是這愚蠢的同義反覆(『生命萬歲』)驅動了遊行隊伍中對共產主義思想仍舊完全無動於衷的人們。」
公平地講,昆德拉寫出來的「媚俗」典範並不只是「冷戰」時代的捷克政府,還包括了一些自以為是的人權鬥士。在他看來,「媚俗」無非就是一種情緒的專制。這種專制的重點不在於控制人民的行為,也不在於控制每個人的思想,而在於控制他們的情緒。以正義和正確之名,它要求大家必須在恰當的場合表達出恰當的情緒,哪怕那些表達有點違心或矯揉造作。就像捷克「五一」節的遊行和人權鬥士抗議赤東的進軍一樣,一定是和某些光明偉大的價值相關。面對著那麼了不起的東西(例如「生命的偉大」),你不「謳歌」不「動情」不「激動」,難道要冷笑要噁心不成?
有意思的是,昆德拉也提到了那種很低賤很下流的庸俗,只不過他把它當成「媚俗」必須拒絕的東西。他認為西方人很難想像亞當和夏娃會在伊甸園做愛,更難想像他們會拉屎,因為這都是些下賤的髒東西,很不符合大家關於樂園的審美理想。他說:「對生命的絕對認同把糞便被否定、每個人都視糞便為不存在的世界稱為美學的理想,這一美學理想被稱之為Kitsch。就其根本而言,媚俗是對糞便的絕對否定:無論是從字面意義還是引申意義講,媚俗是把人類生存中根本不予接受的一切都排除在視野之外。」
那麼我們今天「反三俗」,反的究竟是那些和糞便相關,陰陽怪氣而且取媚大眾的「低俗」?還是排拒低俗永遠向上的「媚俗」呢?我不曉得,可是我隱隱覺得,「旗幟鮮明」地反對低俗和「萬眾一心」地被「感動中國」的英雄所感動,很有可能是同一回事;它是同一種的情緒導向。